编者按:
在2017年2月28日——第十届国际罕见病日到来之际,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作为国际罕见病日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特别推出罕见病日专稿系列。这些文章的作者有医学专家、医药企业负责人、基因检测公司、患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通过这些专家老师各自独特的视角,带我们走进“罕见的世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系黄昱老师的文章。

黄昱,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系讲师,行政副主任,生化遗传实验室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是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和细胞衰老分子机制。
北京医学会医学遗传分会委员,罕见病分会委员。中国溶酶体贮积病研究协作组成员,《中国罕见病》杂志编委,Rett病友会,Dravet病友会,Gaucher病友会,肯尼迪病友会,尼曼匹克病友会,Pompe病友会等多个罕见病组织的发起人或医学顾问,重症肌无力协会监事。
我常自嘲,我是个很无趣的人,羡慕那些在工作之外能把某种爱好玩到极致的朋友们。对我而言,工作就是兴趣爱好,就是修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于我,是远远超出“大学教师”这个角色范围的。其中最有趣的就是“聊天”,有时这种聊天对于对方来说是咨询,比如今天。
这对年轻的夫妻都是即将毕业的名校博士,事业和生活都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他们是人中龙凤,强强联合,没人会把他们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可是,隐藏在学霸招牌下的是一个深深的隐忧,其中一方患有家族性的疾病,可能要到四五十岁以后才会出现症状。是否会影响找工作?医疗保险能覆盖吗?能否生育健康的后代?……我们的聊天,就从这病和基因说起,一直到产前诊断和植入前诊断。
与学霸聊天,这部分的交流当然非常顺利,他们也都查阅过文献,只是在实操部分有些困惑而已。聊天的后半场是我最享受的部分,我们聊高校,科研,入党,70后和80后,婚姻关系,工作选择等等,其中一人自嘲说,自己就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也曾考虑出国,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疾病带来的困惑和隐忧。
对于遗传性疾病,一些滞后的观念、人事和医疗制度,几乎要逼迫如此优秀的人才离开自己的祖国。再优秀再强势的人,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人生的某个时间段,都可能成为弱者。所谓民主,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意义上,都需要做出反思和调整。在聊天的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改变“弱势群体”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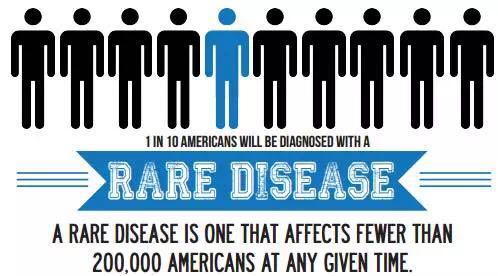
“罕见病”这一概念,在被提出来作为一类疾病进行分类管理时,看似是根据“发病率低”这一客观统计概率,其实是针对“被忽视”“被漠视”这一主观偏见。国内一个时期以来,在讨论“罕见病”的定义时,一直在纠结发病率,就是陷入了这个误区(上海地区已经开始讨论具体疾病列表,不再纠结发病率,值得其它地区借鉴)。用于罕见病治疗的药物被称为“孤儿药”,就是因为在商业制度和文化方面,这类药物像孤儿一样,不被重视,无人认领。
疾病,就是人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社会本无动机再去区分疾病种类是否罕见。但是在照顾患病者的过程中,少数人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包括医疗人员的时间和药物(包括研发生产药物所消耗的资源)。如何界定这些“少数人”,是根据疾病复杂程度?还是根据是否有钱有势?这就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考验社会制度的优劣。医者,一手在感知科学的温度,一手在感知社会的冷暖。科学能解决的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还给社会,大家一起想办法。
人吃五谷杂粮,谁都难免生病,可是每个人得的病为何不同?遗传因素是主因,外部环境是诱因。即使是相同的症状,其背后致病的基因也是相同的。按照遗传因素去细分,每个人都患有罕见病,区别只在于发病早晚和你是否知道而已。
人类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当我们作为旁观者看那些不幸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未来某天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也可能在那一时或一事,成为那个不幸的人。所以,罕见病也是一种态度:是如何科学看待疾病病因的态度,是如何对待“少数人”的态度。
